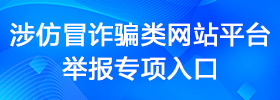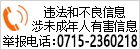稀稀疏疏的老家
今年夏天,遠離社交與喧囂,破天荒在老家住了十多天。
我們?yōu)潮緛砗苄。幼∮旨校郎桨级ǖ姆浚阒杏形遥抑杏心恪S械倪€是共建共享,一個天井幾家共,一個大門幾家出入。擠擠挨挨的,當年有好幾十戶,兩百余人口。
巴掌大的村,老輩人還把它分上屋、下屋與西邊。那時人差不多窮,名字取不出好多花樣,生怕弄混淆了,就加個方位定語。
我有個“上屋婆”還有個“下屋婆”,分別是祖母與繼祖母。上屋己卯,下屋己卯,就分清哪個是人長樹大干莊稼好把式,哪個石磙一樣個子,平素石磙一樣輾不出個屁的老實坨。還有以“新屋”等特殊載體稱的。
這些方位與房屋,在今年隨著最后一個老標記“新屋”的拆建,再無蹤影。我知道,一個有些堅硬而冷靜的新村莊,代替了煙火彌漫嘈嘈雜雜的舊山莊,傳統(tǒng)的某些東西在這里日漸式微。
我熟悉的人先后去了,年輕人大都外出謀生,偶爾相見,他們也許認得我,我卻好久叫不出他們的名字。腦子里總在憶舊,仿佛那些曾憂傷過我的往事,此刻都變成了美酒瓊漿,令人禁不住啜飲。
現(xiàn)在還在村莊長年生活的,不過三十來人,仍然耕作的人都七老八十的。不知會不會出現(xiàn)莊稼完全被雜草侵蝕的現(xiàn)象。
在老家那塊地方,長眠的比活著干事的多,土地長草木的比種莊稼的多,這是我的隱憂。
身處底層,總忽略不了身邊情景,舒心總是多過添堵。
最讓我感到親切的是山巖下日夜啼鳴的斑鳩聲,在電線和房屋穿梭的燕子。斑鳩的咕咕聲加深了村莊的寧靜,燕子翻飛給山村帶來吉祥和靈動,一身黑色羽毛,一雙有力扇動的翅膀,一把剪刀似的尾巴,掠過門前,或停在電線上呢喃,在屋梁下筑巢,無論如何都是能激發(fā)人生活的信心的。燕子以它的輕快身影,不斷提醒和喻示著某種美好向往,某種可喜的境遇。
夏日一個清涼的早晨,山風拂去暑氣,一陣雨澆得小山村煙霧彌漫。燕子悠閑地穿梭于舍間與田疇,或棲于電線桿上。昨晨,幾只燕子飛臨新屋,有尋新家筑巢安家之意。許是感覺吉祥如意,即日喜氣盈門了,它們也來襯托一下氣氛吧。
年近七十的嫂,孤寡多年后,那間散發(fā)霉味的房子,居然有了燕子筑窩,一年一年的從未間斷。這幾年,她每年豐衣足食,種的玉米、紅薯、南瓜、蘿卜等蔬菜,吃不了就帶給我,一部分喂豬喂雞。她健健康康的,還與村里老婦一起跳廣場舞。這似乎是燕子帶來的吉祥。
農閑,這家一個老人獨坐,那家兩個老的坐在門邊,皆不說話。話說了幾十年,差不多說完了,再無閑聊的興趣。若是話匣子被打開,你一言我一語的,又冷鍋爆出熱豌豆,噼里啪啦講起來。
喝酒時,男人話多。一時的紛爭放下了,喝著說著,一方先讓了,被另一人的話岔開了去,于是純粹的沉醉于你來我往的勸酒中。
人老了,眼睛有層霧,耳朵背了,腦子也不好使,常常出現(xiàn)短路,拼命想也接不上茬。八十歲的蓮娘搖著大蒲扇,慢悠悠打我門前過,說:“你這鑼罐真好!”本是說大門,卻說的是鑼罐。
我才交甲子,也常犯混,這回真是一伙老糊涂到了一堆了。
聾子森七十多了,眼神不好,腦子也不靈光,卻喜打撲克,人家說他十回要輸十一回。輸得沒錢了,就找人借了五百元再打。沒錢還了,人家讓他砍柴賣。他跑到山上去砍樹,砍的栗子樹兩尺多圍,鋸成一筒一筒,用了幾天才拖回,放在路邊曬。砍別人樹,人家要講他,終是拿他沒辦法。這是一個從小就有聾子別號的人,講給我這個從小亦有“聾子”別名的人聽的。
那幾天隔絕了與外面的聯(lián)系,眼里只有離得很近的青山,頭上是巴掌大的天空。白天不時飛過雙燕,飛過一些長尾巴的漂亮鳥兒,或一只翱翔的鷹。不去林間,坐在家門口也能見到好多漂亮的鳥兒。白翅膀的,黑翅膀的,長尾的,袖珍的,紅喙紅爪的鳥,它們輕快地穿過綠色玉米地菜地,穿過房舍。一只小小鳥站在電線上,發(fā)出多音階,也能傳得好遠,穿透力不亞于咕咕咕的聲音。在無塵的空氣中穿過的鳥兒,扇起沒有一絲雜念的風。到了晚上,滿天星斗,一彎月,眼前的世界是如此寂寥。
早晨去井里提一桶清涼泉水,燒水做飯,清涼的井水不僅供我們飲用,還用來洗漱、沖刷衛(wèi)生間,這一點真是奢侈至極,心里不禁有些許暴殄天物的負疚。
山村已被打開,出入變得方便了,原來到縣城當天趕不回,現(xiàn)在一個小時足夠。門口一條兩車道公路,不時有大貨車、小三輪和小轎車駛過。有了新公汽,老人沒事時坐上車免費去縣城逛一圈,誤不了回家料理家務。
趁著早晚天涼,老人們下地干活,給莊稼除草澆水一線施肥。芒花已枯,割下來扎帚。再過些時,收地里豐收的玉米。這好年頭,養(yǎng)好身體。老人們想的不過如此,能動就干點事,不必太辛苦。
到了晚上,照例要納涼,人多的地方聚了五六個,大抵說的村莊過去,說往日的奇聞奇事。說起蛇,有扁頭風,金環(huán)銀環(huán),土骨蛇等。有只黑風哨,有刀把大。有人說,不對,有胳膊粗。谷子剛黃時,蛇在稻田里出沒,我娘嚇得跑回家,驚魂未定地講給人聽,大家跑一公里去上畈田看,大蛇還在谷田里,見了人便逃遁,蛇爬過的地方,稻谷被壓倒一片。
有人說蛇追光,電筒一照,它猛地竄起好高,向亮處撲過來。
又有人說,大反哥總是把“自必然”掛在嘴上,每每大家坐在一起,談論年成,談論天災人禍,哀聲嘆氣的。他便說:“不埋怨,有個自必然的。”自必然,在這里是“車到山前必有路”“一顆草必有個露水珠”“活人哪會被屎尿憋死”。總之,勸你別杞人憂天,天無絕人之路。
聊著聊著,又聊當今,漸漸的疲了各自散去。時光就這么日復一日過了,六十年,八十年,九十年,老人們在時光里不斷被人提起。
世界這么小,又這么簡單,所聞無非雞毛蒜皮,所見亦有限,我隨心好了,有家鄉(xiāng)作底子呢。
作者:孔帆升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