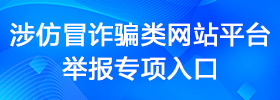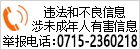鄭安國:故鄉,及其他
故鄉,及其他
作者:鄭安國
一 ?
無論怎樣,我都是很愿意回到隱水的。
盡管那里曾經蔥郁的青山變得光禿,除了滿目的野荊和裸露的山體,已聽不見貓頭鷹的叫聲,看不見野豬和山兔箭一樣射過清清澗峽和樅樹林。那些從前牧歌悠揚的美麗阡陌和田垅,此時被荒草彌漫,村莊上空斜著幾縷炊煙,這偌大的村落,除了幾聲犬吠和雞啼,只有人語寥寥。從前澗邊山頂高曠悠揚的山歌呢?它們都消失了么?
父兄們哪里去了?童年伙伴哪里去了?姊妹們哪里去了?
踏著微現著白霜的山路,我感到一種凄清和落寞,這條路不知走過多少代人了,它依然仄狹不平。多少年來,只有游子循著這條臍帶來尋自己的根,如今父老鄉親卻沿著它走向山外,仿佛雁陣橫過黑土地,有些永遠不再返回,有些成為村莊的另一種候鳥,飛得憔悴飛得沉重。我不明白為什么我的父老鄉親寧愿在異鄉的屋檐下仰望明月或聆聽淅瀝的雨聲,嘗那份背鄉離井的酸楚,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鄉。
我無言。但我深知,生活永遠是美好的。
我的父老鄉親世代勞作在田園,無怨無悔,忍辱負重,心底寬厚地面對世事,但他們有他們的尊嚴和對世道人心的認知,他們把困惑和希冀埋在心里,艱難地寫著他們的人生。
許多代人已老死在逼仄的田園里,許多的旱澇和災禍都挺過去了,但如今兄弟姐妹卻候鳥一樣飛離故土,漂泊在陌生的異鄉,他們是存著一份向往,也懷著一份無奈吧。
許多的父兄和叔嬸都死去了,山坡上的新墳和舊墳在寒夜里閃動著磷火,他們奉獻了一生。生前吃苦太多,死后卻很冷清,他們的后人都到山外去謀生去了,已差不多忘了埋在土里的親人,就像忘了遺落在責任地里的紅苕和花生。
許多的姐妹都已嫁了人,她們都用不太美麗卻賢惠的青春在很遠的村村落落勞作,生養后代;甚至她們在很大的城市里花枝招展,在花花世界里盡情任性。如今她們已消失在異鄉人海,我已再見不到她們的面容。
我無法追回這逝去的一切。
人不能安守清貧的時候,便學會流浪。村莊就像一部古舊的農書塞在山縫里,只有歲月的風在無聲的翻弄。
我不知道這世代播種著汗水和淚水、收獲了貧窮也收獲了快樂的田園為什么被人離棄。田園,美麗且蒼茫的田園啊,你到底怎么了?是你的泥土不再養人,還是你中秋的明月不再渾圓?是你的阡陌不再美麗,抑或是你的山歌和炊煙不再溫馨?為什么沒有了眷戀,為什么人要逃離你的庇護,寧愿去漂泊?
在寂靜的月影里,我凝望著這依然美麗無言的村莊,想起它落著大雪時的動人景象和春花灼灼的晴日,想起童年的嬉戲和無憂,想起許多的人和事,我仿佛明白了人或許是應該離開故土的,只要心中裝著,哪怕在天涯,也會感覺著它的存在和召喚。我和那些兄弟姐妹一樣充當著游子,可是這腳下的田園永遠以無言的美麗和親情召喚著遠方的靈魂。
人,譬如我的那些父老鄉親,他們只有一群斂翅棲息在故鄉的候鳥。
二 ?
人都是候鳥,終是有離開的。
只有一樣是我無法與之孤隔開的,那就是大地。我一輩子都會在大地上行走,直到將來某一天,我走不動了為止。
少年的時候,不知愁滋味,整天只有無邊際的幻想和憧憬,像天空里變幻不定的云彩一樣,我沒有認同一樣將來的歸宿。大地對于我來說是平坦無邊的,任我游移和騁馳。面對一個無邊的大地,一個孩子的內心里充滿了激動和好奇。我一個人在收獲過的麥田里過夜,在麥垛上呼吸著清涼的夜風,昂頭注視著滿天的星星,在黑暗里聽到大地的秘語和星星的歌聲。夜風傳來了遠處村莊的動靜,稀稀落落的犬吠和人聲已經遙無可辨。樹葉在風里的呼嘯已經成為夜語中最為宏大的動靜,黑暗中,眼睛失去了觀察了對像,我聞得到花香以及遍地麥茬的氣息——散落于麥地之間的麥粒、野草、被踩死的螞蚱和腐爛的蚯蚓,我卻聽見了花開的聲音以及這些細微的變化,在被水浸泡和腐敗時產生的細微的動靜,有時候,可能自己聽到的一切都只是一種幻聽,就像在極靜狀態時,耳朵里會產生一種嗡嗡的轟鳴一樣。幻聽其實是一種心靈感觸到的聲音,有時候,在夜里,會聽到自己心臟跳動的脈搏聲,像潮水一樣起起落落,各種神秘的液體管道貫通全身,它們日夜流動著。可是,我相信,在那一個夜晚,我聽到的聲音全是來自于真實世界的。大地在呼吸,不是么?這呼嘯的風就是它澎湃的氣流;大地在歌唱,遠處近處的蟲吟和樹葉的婆娑、河水的波浪撫摸著堤岸、花朵在夜風中搖曳……聲音來自于心動,這就是那宗著名的禪宗辯語“非幡動、亦非風動,乃是心動”,大地之心在動了,我的心也在動了,于是,我聽到了大地之語、大地之歌。那一夜,我似乎成熟起來了,我聽到了一個真實的世界之音。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個智者指示我,這就是大地——萬物之母,一個能夠產生無窮生命的大地的私語。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的前生和來世,在大地的此端和彼極,有無數的聲音在響起,連貫成海。
清晨,早起的我看見了一輪紅紅的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群山眾壑為之動容,天空中布滿了橙色的光輝。大地誕生了一顆新鮮的太陽,那連綿的晨風是不是它分娩時微微的呻吟?那一輪太陽像一枚雞蛋黃一樣,柔軟無比,大地在某一處砉然開裂,從產門處娩出這一枚太陽。凝穆的大地,我聽不見它深夜里的呻吟,清晨里的樹佇立不動,萬物肅靜,在注目著萬物之靈的誕生過程。
此時,大地靜得只聽得到自己的心跳,我的心跳在一次次地沖擊著肺腑,血液像隱秘深處的河流澎湃激蕩。大地在疲憊地喘息,清晨的微風拂過大地,霧氣蒸騰,那是大地升起的汗水。河流在靜靜地流淌,田野上的樹、草和花朵在歡呼,這種聲音只藏納于一種大音的背景之中,我看到空氣流過大地形成的旋渦,風夾著輕塵扶搖而上,樹葉、草和花朵在搖曳中微微顫栗。陽光輕輕踩過疲憊的大地,在它母親的乳房和胸脯上踩著,大地歡愉地裂開一條條細縫,一種斫裂的脆響從地底下向上傳遞。大地富有彈性的肌膚將陽光向上彈起,光芒越過村莊和河流,直向遠方。

三
普里什文在《大地的眼睛》說:“一切者聽得見,一切者看得見。”“春天的光明、樹葉從枝梢萌動的微響,小鳥啄破卵殼而出的第一聲嫩啼……森林里的水滴,泥土里鉆出來的昆蟲在摩擦著翅膀。”“一片花瓣掉落在草地上,敲彎了另一棵草的腰。”“布谷鳥的聲音像一些不連貫的音符,撞擊著窗戶邊緣的冰凌,土地裂開了無數條縫隙。”他是一個大地細微的觀察者和聆聽者。經常在森林里出沒的人都會有一種體會:那就是樹葉生長的聲音是清晰可聞的,一個無意坐在草地上的人會突然感覺屁股底下有什么東西向上刺痛他,起身一看,原來是剛破土而出的春筍。
樹葉萌芽的時候,在一夜之間,所有的樹葉都爭先鉆出堅硬的樹皮,迅速地舒展開,那種積蓄已久的力量是驚人的,它們在發出一種持續的聲音,這是一種次聲波,它能夠傳播得更遠,在方圓數百里的大地上,這種記號或者說是大地的暗語在傳播著。在地底下,蠢蠢欲動的樹根同樣也在擴張著,膨大并繼續延伸,向更深更遠的地方探入。泥土脹裂的聲音同樣是次聲波,是超出我們聽域的秘語。大地在改變著,這些秘語在無聲地傳播向遠方。在春天,收拾大地上意外生長出來的菌株,經如松蕈,在松林岡上細心地尋找,那些其貌不揚的家伙就混在掉落的枯松針底下。有經驗的人會用耳去聽這種動靜,當它頂開地表的落葉和泥土的時候,會有一種細微的聲音。春天的時候,收筍人在繁密的竹林里尋找恰在此時好冒出土的新筍。竹筍出土的勢頭很強勁,像動物一樣迅速,一夜之間竟可以長高數尺,夜深人靜的時候,聽到竹林里一片砉砉的聲響,那是竹筍在拔節。竹籜爆開時,發出一種脆響,像折竹之聲,竹節吸過雨水后,極速膨脹伸長,聲音嘩然。所以,尋找竹筍不是件難事。有時候,砍下來的竹筍背在背簍里,還在長,身后一片竹籜迸裂的聲音,竹林人說,瞧,竹筍成精了!山里的萬物生長皆不徇定規,曲折成長,或快或慢。曾經聽到一個山民說:他上山時曾經將一把砍刀忘記在某棵樹下,再也無法找到了。后來,有個人伐倒一棵樹,在樹心里找到那把已經銹蝕的柴刀,樹已經將它慢慢吞噬了,樹吞刀的事情,應該不會是不動聲色的,一定會有一番尺風雨的搏殺,最終,柔軟的樹“吃”掉了堅硬的鋼刀。
在梅山峽的觀音巖下,有許多人將折下的樹枝倒插在巖縫的泥土里,讓這些樹枝“支撐”起巖石的重量。有些枝枝竟然長出根來,成為一棵異乎尋常的小樹。這些樹竟慢慢地向上曲折伸長,最終彎成觸目驚心的造型,當地人稱這些樹為“撐腰樹”。一些巖石被樹撐下來了,堅硬的巖石竟也拗不過這些柔軟的樹枝。這其間一定也會有驚天動地的較量,能夠將巖石撐裂的力量不容小視。可惜,我竟聽不到這種慘烈的聲音。
曾經認識一位老僧,他有一個癖好,就是在山里孤巖上打坐入定,我問他:僧有所聞?僧不語,等他睜開眼睛,他說,我是在和大地交談,他聽風語、樹語、野草語、花語、巖石語……我奇訝:石能言乎?僧點頭,能言,你且看,那遍山的草木能語乎,草木生于石上,故石也能語。我環視四周:巖上蒼苔可人,巖縫中還有星星點點的野百合和骨碎補,在風中裊娜不已,《曇宗秘錄》中說:“無一切語,無一切不可語,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石無一切語,其實石語一切,我們聽到的是語,聽不到的也是語,只不過那需要用心去領悟。佛說聆聽諸相,有關心語為最,用心聆聽,就是悟的過程。一棵樹能生云,是奇跡么?非也,是因為云知道樹不會掛礙自己,想想,倘若云知道一旦沾上了樹就再也脫不掉時,那片云肯來冒這個險?同樣,如果處處皆可聞語,那么,就是一種吵雜無序的噪音了。這么說下去,就有點玄了,打住。隨眼皆風物,處處有禪音,這就是自然的物語了。
大地之秘語,是可聞,亦不可聞。
四
一場山火過后,山野一片狼藉,處處是燒成黑炭的樹木殘骸和動物尸體,地上是一層厚厚的炭灰。那一夜,山上風呼樹駭,走獸奔突,慘叫聲不絕于耳。大地在烈火的炙烤下坼裂涅槃,生命消失了,地底下的蟲蜇也隨之燔成灰燼。可是,過不了多久,這里又會長出茂盛的野草,新的樹會從殘根部萌生出來。再過數年,一切將恢復原樣,又是一片草木崢嶸、繁花盛開、藤蔓羅地、飛禽走獸竟逐于此。
火是一種最冷酷的語,是大地最徹底的沐浴和更新。火語為何?火是一種極端的結束方式,是生命與非生命的一次大轉變,想必,樹木在火中一定會慘號驚呼,生命力旺盛的野草也難逃一劫,野草畢畢剝剝地燃燒,隨火焰而舞,這是一種放達的哀歌,視死如生,就是野草的性格,樹的身體在火中化為炭灰,這一定要忍受極大的痛苦。這種哀語孰能聞之?大地靜默無聲,雖然它同樣也要承受著劇烈的疼痛。
諸般痛苦,只在一瞬間,生者亦痛矣,死者渾若睡。天地不仁乎?有時要作這樣想:天地是不會特意去關照一個生命的生與死,天生地育,那是造化的本能。一切變化都是一種緣分,生是,死亦是。天語為震霆,地語為風。在三明萬壽巖古人類活動遺址,我看到了三萬年前的先人們在地穴里燔火的痕跡,他們留下了許多石器和動物的骨骸化石,這些已經消逝于時光長河里的鏡像竟會在我的眼前一一幻出,茹毛飲血的時代,他們作為智慧的靈掌類動物之長,還處于鴻蒙未昧的時期,不會想太多的事情,他們只是為了果腹,才創造出了那么多工具來。他們用硬石來磨礪另一塊硬石,在火星四濺之下,在空空的敲擊聲中完成了第一件工具的制造。他們不會留心那動聽的石擊聲,不會為大地即將誕生人類而歡呼。大地在那一刻一定是欣喜若狂,畢竟,從此以后,萬物有了主宰,萬靈之靈即將誕生。
我注意到了,那是一些普通的鵝卵石,青色的和黃色的石錛、石斧、石刀是一種艱難的敲擊的結果,這里頭已經融入了人類早期的智慧。因此,它們看上去一點也不比我們現在的一切工具遜色,想想,如果讓我們現代人不借用任何工具,僅憑一雙手去制造這些石器,又有幾人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呢?遠古的聲音已經消逝,遠古的骨骼已經化為堅硬的石頭,這個洞穴能與否?我佇立于洞中,聽到的是洞外的風聲樹語,鳥語花香。可是我相信,這些石器一定記憶下了那段歷史。考古學家從那些簡單的石器造型上解讀著三萬年前的秘密。
春天過后,遍地的蘆葦紛紛抽出或紫或灰的花序,像許多隱寓秘語的旗幟。大地生長出更多的花草樹木,那些雀舌黃楊、木荷和青岡櫟抽出紅艷似花的新葉來,這分明是一種歡悅的語言,來自于大地深處的秘語。花開的時候,山野里有許多種鳥在鳴叫,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地之語已經幽微難辨了。我聽得滿耳的風聲、樹聲、草聲,聽到水滴巖石的脆響,聽到水流淙淙,大地開始新一輪的孕育期。就在此刻,我敲擊著電腦鍵盤,聽到的窗外樹葉的呼嘯,狂風驟起,那種隱隱的聲音自遠方傳來,我在靜靜地聆聽著、記錄著。
上一篇: 德不孤,必有鄰
下一篇: 李城外:“鐵桿”金戈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