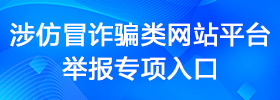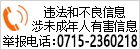《鄉村深處》之阿華
作者:孔帆升
老家吳家山是個狹長山村,我認為是祖宗苦著臉把基因傳下來,才使后代長著個長臉。男人們走路,吃飯,趕著牛在河堤上走,夾著柴刀上山,都抿著嘴,低著頭,慢吞吞地拉著長臉,仿佛在隨時準備撿起地上的失物。
阿華平常是低頭漢子啞巴爺,呼風卻是老手,大熱天站在山坳上張開喉嚨,用手筒在嘴上做喇叭狀,然后拖長音調“嗚一一喂!”幾里路外的風立馬趕過山梁來到身邊。他說話總差把火,不是聲如蚊蠅,就是嘴巴縫上了。仔細觀察,他還是喜歡說的。或者他原本就不想發出任何聲音,嘴唇輕微蠕動,以腹語傾瀉心頭堵塞的情緒。有時,眼神里是一團向下壓的霧,臉陰沉沉的,老大不高興,可能是受了欺負,也可能是被人誤解了,還有可能是好端端的被別人一個臉色弄得煩惱從生。他向來十分小心,走路都怕踩殺了螞蟻,更別提惹身邊那些活生生的人生氣了。
阿華結婚生子后,心里縱有千般丘壑萬般刀刃,也都化作一團氣憋住,憋出屁也要悄悄地到沒人的角落去放。有人笑他木訥,呆板,一根筋,屢用話語激他,他只抿抿嘴唇,露出無奈的笑。轉個背,就忘得一干二凈,該干什么干什么去,第二天像什么也沒發生過一樣,見了譏諷的人還點點頭。這么老實的人在大公社時自然輪不上被告黑狀,免受批斗與欺負之罪。
某年,誰也沒想到他居然肯當生產組組長。一個灣子總得有個領頭人,原來叫隊長,現在叫組長,這職務沒多大變化,大概就像千萬個家庭的家長一樣平常。隊長權力大,記工分、派工、鑒定社員身份、推薦上工農兵大學,很是吃香。我記得父親做木匠是吃香的,他還要常請隊長來家里喝一盅,隊長常半推半就地來打打牙然。用我媽的話說是:“人家一年到頭看不到你一盅酒,那是不行的。”隊長變為組長以后,就沒人稀罕了,送醋一樣,好多年都沒人當,人家都叫組長為維持會長,好些村子里實在沒辦法選人就抓鬮,輪流坐莊,過著“黃豆年年黃,黑豆年年黑。”的日子,誰閑操那份心哪?!
吳家山的組長也是輪著當,很多人都當過,用他們的話說是“這山旮旯鳥拉屎都不生蛆,種子再好土地瘦,沒法子。”阿華當組長是幾個房頭輪著輪著到他頭上的,推不掉,只好上架。可想而知,自然是很傷腦筋,處處遇麻煩。他家庭出身貧寒,沒讀多少書,本就做不起人,又無好親好友,顯得無比的人單勢薄。不善言辭的他,碰到刁鉆蠻橫的人,更是豆腐掉到灰里,無從著手。“我自己都討厭自己”,每到一地雞毛一籌莫展時,有人會聽到他這么自言自語。不是聲音高得讓人聽見了,而是那兩片厚唇多次啟合,離他近的翻譯出大約的意思。評困難戶低保戶,那些孩子在外創業條件好的人,因年老多病也爭名額,還大罵繁華狗眼看人低,他氣得臉通紅,青筋突暴,最后還得孫子一樣乖乖上門做解釋工作。也有那真正苦的低保戶被群眾代表評落了,人家傷心地上門哭訴,阿華只好熱臉貼人家冷屁股,硬著頭皮帶他一級級求情,倒貼時間與盤纏也不惜了。
一兩年組長當下來,吳家山江河依舊,他自家里好多事沒料理,組里什么也不多什么也沒少,阿華身上倒是滿身的受氣包。誰都朝他撒氣!老婆像罵兒一樣罵他沒用,群眾嫌他不公心又怕事,村干部在鄉受了氣也要發泄在他身上。這受氣包也是人經沙場練就的金包,一罵就把他罵得世界空空,萬物無形,只盯著腳下的土地發呆,不一會就全身長滿棘刺。再一會,刺人的棘刺變成了花,阿華簡直成了拈花一笑的姑娘。風輕云淡,一切安好!阿華最好的朋友就是家里的一條狗,無論走到哪都跟到哪,他干活,它蹲在一邊吊著個長舌,拿一雙水汪汪的眼看他。他去鄉里回來,狗像久別親人一樣圍他轉,晃頭晃腦,扭動腰肢,一個勁兒搖著尾巴,渾身的勁兒使不完。阿華煩惱時悶著頭抽煙,常常盯著狗一看半個時辰,那山般沉重的絨默里,有著無盡的惺惺相惜。
那些年旁邊村子都紅紅火火的,唯獨吳家山夕陽依舊,阿華急得結結巴巴打電話要我操操心,我也有點急,回了趟老家。阿華見面如舊,一句“冬聲回了”,再沒二話。找他細聊,他竹筒倒豌豆傾出宗宗件件“人心散了”的細節,他說:“過去是費力不討好,所以無人為頭,現在有甜頭嘗了,讓別人去當吧。”阿華果然說不干就不干,灣子里半年沒人理事。我作為八十年代就離鄉工作的一員,受委托主持群眾代表會,一屋人抽了一地的劣質煙,開始票決,70歲的退休教師阿白票選過半,他猶豫再三不肯當,阿華幾個代表軟磨硬敲,最后他表了態當上了新組長。阿華不像那些下臺的干部專找臺上的岔子,凡事都支持集體。從此村子里真正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路寬了,路燈亮了,廣場大了,橋加固了,塘修復了,水庫下面的渠道疏浚了,山林也流轉了。70多歲的新組長在欣喜之余,免不了向人謙虛與藝術地炫一下:“是冬聲把我推到火上烤的。”當他說了多次后,我告訴他:“是阿華推薦的,要烤就拉上他一起烤吧!”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
鄂公網安備 42122402000111號